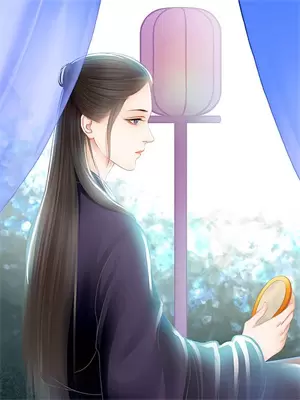1夜色如墨,笼罩着青藤大学的东区宿舍楼。六楼拐角的窗户大敞,窗帘在风中翻飞,
像一具无声招手的白袍幽灵。警戒线早已撤去,可那股铁锈般的血腥味,
仍固执地黏在墙缝与地砖之间。沈之一站在楼下,仰头望着那扇窗。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,背着旧书包,模样清瘦,眼神却沉得像深潭。他不是来祭奠的,
他是来确认——确认他弟弟最后看到的世界,是不是也这样冷。三天前,
这里发现了第三具尸体。沈之言,20岁,大二学生,死因:高处坠落。
警方通报称“因学业压力过大,抑郁自杀”。校方迅速结案,家属签了字,葬礼低调举行。
可沈之一知道,他弟弟从不恐高,更不会在期末周的深夜,独自站在六楼窗台。
他走进宿舍楼,宿管阿姨打量他:“新生?这层封了,别上去。”“我找人。”他声音平静,
“我哥住这儿,说留了东西给我。”阿姨犹豫片刻,放他通行。六楼走廊空无一人。
307室门上贴着封条,他轻轻撕开一角,推门而入。房间整洁得诡异。床铺叠得如军营,
书桌一尘不染,连垃圾桶都被清空。可沈之一蹲下身,
用指腹擦过床底边缘——一层极薄的白色粉末。他眯起眼,掏出随身小瓶,取样。
这是碳酸镁粉,常用于攀岩或体操防滑。可弟弟从不运动。他拉开书桌抽屉,
一本日记被藏在夹层。翻开第一页,
是弟弟的字迹:“他们说实验不会留下痕迹……可我开始梦见自己在坠落。
”沈之一的心跳慢了一拍。他记得弟弟最后一次通话,语气异样:“哥,
我好像……不是我自己了。”当时他只当是压力大,随口安慰几句便挂断。如今想来,
那不是抑郁,是被操控的前兆。窗外,一道黑影掠过树梢。沈之一猛地抬头,
只见六楼平台的边缘,似有白影一闪而逝。他冲出门去,楼梯间空荡回响。跑到平台,
只余风声。地上,却多了一张折叠的纸条。他捡起打开,
上面是一行打印字:“第三道题:当所有人都认定是自杀时,真正的凶手,
正在观察下一个观察者。”背面,是一道逻辑谜题:“A说B在说谎,B说C在说谎,
C说A和B都在说谎。谁在说真话?”沈之一盯着那行字,嘴角缓缓扬起一丝冷笑。
“有意思。”他将纸条收进衣袋,望向远处教学楼的灯火。弟弟不是自杀。这也不是终点。
而他,已经踏入了凶手的棋局。2青藤大学的九月,梧桐叶开始泛黄,
风里带着图书馆旧书页和咖啡厅烘焙豆的混合气息。沈之一背着书包,
走在新生报到的人流中。他换了名字——“沈默”,
档案上是某重点高中因心理评估延迟入学的学生。校方不知,这个“沈默”,
早已把他们的漏洞看了三遍。他被分到东区宿舍306,与307仅一墙之隔。
搬进来的第一天,隔壁男生主动敲门,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。“你好,我叫林砚,
大四心理系,住你隔壁。”声音温和,像秋日午后晒过的棉被。沈之一接过咖啡,指尖微凉。
他打量对方:白衬衫,黑框眼镜,发丝整齐,笑容恰到好处——标准的优等生模板。
可那双眼睛,太静了,静得不像年轻人该有的样子,像一口封死的井。“谢谢。
”他低头吹了吹热气,“刚来,还不太熟。”“理解。”林砚靠在门框上,
目光不经意扫过他行李箱角落的旧标签,“你是转专业进来的?档案说你原本报的是计算机。
”沈之一心头一震。档案本该保密,连辅导员都不该随口提起。“嗯,
后来觉得……人比代码有趣。”他轻笑,“你呢?大四了,还不搬出去?
”“我在做毕业论文,导师建议留校。”林砚语气平淡,“研究‘群体认知偏差’,
挺无聊的。”沈之一眼神微动。群体认知偏差——正是弟弟日记里提到的实验关键词。
“有意思。”他放下咖啡,“你觉得,人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误导?”林砚终于正眼看他,
嘴角微扬:“当他们坚信自己在独立思考的时候。”两人对视三秒,空气仿佛凝滞。那一刻,
沈之一确认了一件事:这不是个普通学霸。他是猎手,只是披着温良的皮。接下来几天,
沈之一刻意放慢节奏,像普通新生一样上课、吃饭、去图书馆。
他选修了心理学导论——林砚也在。课堂上,教授讲“认知失调”,
林砚突然举手:“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是正义的,却持续伤害他人,他是疯了,
还是被系统扭曲了?”全班安静。教授笑了笑:“这是个哲学问题。”林砚坐下,
笔尖在笔记本上轻轻点着,像在打摩斯密码。沈之一盯着他侧脸,
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:林砚记笔记时,从不写“我”字。所有第一人称,
都用“观察者”代替。——“观察者记录:今日课堂讨论引发情绪波动。
”——“观察者推测:教授回避核心问题。”这不是习惯,是身份剥离。
一种典型的解离倾向。下课后,沈之一故意落在后面,翻看林砚留在桌上的笔记。字迹工整,
逻辑严密,但每页边缘都画着极小的符号:一个倒置的钟,和三道划痕。
他想起弟弟日记里的一句:“实验第三阶段,他们让我们画‘时间的反面’。”他正出神,
林砚去而复返,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把伞。“要下雨了。”他说,“你没带伞。
”沈之一抬头,天空阴沉。他接过伞,道谢。“不客气。”林砚微笑,“不过,
你最好小心点。这学校……有些路,看着是通的,其实是死胡同。”说完,他转身离开,
背影融进灰暗的天色。当晚,沈之一在宿舍用显微镜分析那层碳酸镁粉,
同时比对林砚的笔记照片。他发现,那些符号的排列,竟与弟弟日记末尾的涂鸦高度相似。
他打开电脑,调出青藤大学近三年的心理实验审批记录。在一堆正常项目中,
一个名为《认知边界与群体服从性测试》的课题引起他的注意——负责人:心理系教授周临,
参与学生:五人,其中四人已死。第五人,正是林砚。他盯着屏幕,指尖发冷。这时,
手机震动。一条匿名短信:“你弟弟死前,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”没有署名,号码已注销。
沈之一缓缓闭上眼。他知道,自己已经不是在调查案件。他正在走进一场,
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局。而林砚,不是嫌疑人。他是钥匙。3青藤大学的秋天,
总在雨水中发酵出一种陈旧的气息。图书馆三层的阅览室,因年久失修,窗框锈蚀,
每逢雨天便渗进细密的水痕,像时间在木桌上爬行的足迹。沈之一选了这个角落,
不仅因为僻静,
更因这里曾是弟弟沈之言最常来的地方——根据宿舍管理员无意间提起的一句话,
他已在此蹲守三天。他摊开一本《群体行为与认知操控》,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打印纸。
那是他从弟弟加密硬盘中恢复出的唯一一张合影:五名学生站在心理实验楼前,笑容僵硬,
眼神躲闪。背景里,教授周临站在台阶上,手搭在其中一个学生肩上,姿态像在加冕。
五个人中,三人已死。第四人,是林砚。第五人,是个女孩,穿白衬衫,站在人群边缘,
几乎被树影吞没。她叫程雨柔,应用心理专业,大三,也是目前唯一活着的实验参与者。
她的左耳后有一颗小痣,照片上不明显,
但沈之一在弟弟的日记插图里见过——那是一幅铅笔素描,题为《她看不见自己的影子》。
沈之一正盯着照片,门被轻轻推开。是林砚。他端着两杯咖啡,一杯递来,
热气氤氲:“又见面了。你在看……老照片?”沈之一不动声色,将照片收起:“随便翻翻。
你认识这些人?”林砚眼神微闪,极快地掠过照片一角,然后摇头:“不记得了。
老照片而已。”“可他们都是心理实验组的。”沈之一盯着他,“你不是也在?
”空气凝滞了一瞬。林砚笑了,坐下,把咖啡推过去:“你调查我?”“我只是想知道,
我弟弟死前在做什么。”沈之一声音低,“他日记里写,实验会让人‘看见另一个自己’。
你经历过,对吗?”林砚没答。他低头搅动咖啡,动作缓慢。良久,
才轻声道:“你弟弟……不是第一个想逃的人。”“逃?”“逃出实验。”他抬眼,
镜片后的目光忽然锐利,“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?不是实验本身,
而是你开始怀疑——逃,是不是也是实验的一部分?”沈之一心头一震。就在这时,
窗外一道闪电劈下,暴雨骤至。灯光闪了闪,阅览室瞬间陷入昏暗。黑暗中,
林砚的声音轻轻响起:“沈默……你有没有试过,分不清自己是观察者,
还是被观察的实验品?”话音落,灯亮。林砚已起身,留下一句话:“如果你真想查,
去档案室。但小心——有些门,打开就关不上了。”他转身离去,背影消失在雨幕中。
沈之一坐在原地,手心微汗。他调出手机,拨通一个号码:“帮我查程雨柔,活着的第五人。
她最近……有没有去看心理医生。”半小时后,消息回传:“程雨柔,
三个月前开始定期就诊于校外‘宁和诊所’,主治医师:林砚。”沈之一盯着屏幕,
呼吸微滞。他点开诊所官网,照片上,林砚穿着白大褂,站在诊室门口,微笑温和。
简介写着:“擅长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与解离性障碍治疗。”——解离性障碍。
他猛然想起,弟弟日记最后一页,潦草写着:“林砚说,他每天醒来,
都要问自己三次:‘我是谁?’”原来,林砚不是参与者。他是观察者。而程雨柔,
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“实验品”。当晚,沈之一潜入心理系档案室。门锁是老式机械锁,
他用弟弟留下的工具包轻松打开。月光从高窗洒入,照在成排的档案柜上。
他找到编号“X-07”的抽屉——那是实验项目的归档编号。里面没有文件。
只有一张新的照片。五个人的合影,但这一次,第五人被涂黑了脸。而照片背面,
用极细的钢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第四阶段:诱导观察者成为执行者。”字迹,
与林砚笔记中的笔迹完全一致。沈之一的手指颤抖。
他忽然意识到——林砚不是在治疗程雨柔。他是在复制实验。而他自己,
可能早已被纳入新的观察名单。4宁和诊所藏在城西一条老巷深处,
青石板路被连绵秋雨浸得发黑,两旁梧桐树影婆娑,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。
诊所灰墙爬满常春藤,叶片在雨中微微颤动,仿佛在呼吸。门铃是老式的铜铃,
一响便发出悠长的回音,像是从记忆深处传来。沈之一坐在候诊室,
手里攥着弟弟沈之言的旧素描本,封面已磨出毛边,页角卷曲。
他以“焦虑症患者”身份预约了林砚的门诊,编号:07——与实验项目编号相同,
他不确定是巧合,还是某种暗示。候诊室墙上挂着几幅抽象画,笔触凌乱,色彩压抑,
像是被强行压抑的情绪在画布上爆裂。沈之一忽然怔住——其中一幅画的角落,
画着一个倒置的钟,时针指向七点零七分,与林砚笔记边缘反复出现的符号一模一样。
他翻出手机,对比照片,心跳加速:那符号,出现在弟弟日记最后一页的涂鸦中,
也刻在心理实验楼地下室的金属门上。他翻开素描本,快速翻页。
验室记录数据、周临站在讲台前——逐渐变为扭曲的面孔、重叠的影子、被锁链缠绕的大脑。
最后几页,全是同一个场景:一间白色房间,四面是镜,中央坐着一个人,头低垂,
肩胛骨处有编号——X-07-4。那是林砚。而房间的角落,总有一个模糊的背影,
穿白大褂,手持记录板。那人从不露脸,但沈之一认得那枚袖扣——青铜蛇缠绕权杖,
心理系教授周临的标志。更诡异的是,那袖扣在每幅画中都微微反光,仿佛在注视着观画者。
“沈默先生?”护士轻声唤他,声音像从水底传来,“林医生请你进去。”诊室很暗,
窗帘半拉,只一盏台灯亮着,光线聚焦在林砚面前的病历本上。他穿着白大褂,
镜片后的目光温和,却像在评估一件精密仪器。“最近睡得怎么样?”他问,声音平稳,
带着某种节奏感,像在引导催眠。沈之一低头,声音微颤:“梦里总有人问我……你是谁?
”林砚笔尖一顿。他抬眼:“这个问题……你弟弟也问过。”空气骤然凝固。
沈之一缓缓抬头:“你承认认识他?”林砚合上病历本,轻叹:“我不该瞒你。
沈之言……是我带进实验的。但我说服自己,那是为了救他。”“救他?
”“他有严重的解离倾向,记忆碎片化,常说自己‘不是真正的自己’。”林砚目光低垂,
指尖轻轻摩挲袖扣,“我试图用实验帮他整合人格。
可我们低估了系统的吞噬力——它不整合,它替换。”“系统?
”“周临的‘认知重塑计划’。”林砚终于说出真相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,“它不是研究,
是筛选。筛选能承受‘身份替换’的人。失败者,会彻底分裂,或自杀。
成功者……成为新的观察者,继续筛选下一人。”沈之一心跳如鼓:“所以你活下来了?
”“不。”林砚苦笑,摘下眼镜,眼底布满血丝,“我只是还没被替换完。
程雨柔是最后一个测试对象。如果她通过,我就能‘退休’。如果她失败……”“她会消失。
”沈之一接上,“像前三个一样。”林砚闭上眼,沉默是默认。沈之一猛然起身,撞翻椅子,
木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就在这时,诊室门被推开。程雨柔站在门口,脸色苍白如纸,
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白衬衫,袖口磨损,发丝被雨水打湿,
贴在额角。“林医生,”她声音发抖,“我……我又画了那个房间。”她递出纸张。
沈之一低头——纸上是那间白色房间,但这次,中央坐着的人是他自己。而角落的背影,
换成了林砚。袖扣仍是青铜蛇缠绕权杖。更可怕的是,房间的镜面中,
映出第五个人——一个模糊的影子,站在沈之一身后,手搭在他肩上。那是周临。
沈之一脑中轰然炸响。他忽然明白——他不是在调查实验。他就是实验的下一环。
林砚看着他,声音极轻:“你弟弟最后画的,不是房间。是继承仪式。”“什么继承?
”“观察者的位子。”林砚缓缓站起,“沈之言失败了。程雨柔如果失败,轮到你。
而我……终于可以闭上眼。”程雨柔突然抓住沈之一的手,
指尖冰凉:“别信他……他上周开始,不再记录我的梦境。
他只问我——‘你看见谁在镜子里?’”沈之一浑身一震。
他想起弟弟日记里的一句话:“当观察者开始问‘你看见谁’,说明他已看不见自己。
”当晚,沈之一回到出租屋,将素描本摊在桌上,用紫外线灯照射最后一页。在暗光下,
一行隐形墨水浮现:“07-4 已激活,07-5 待确认。
替换程序启动倒计时:72小时。”下方,是林砚的签名。而日期,正是今天。5凌晨两点,
城市沉入雾海,唯有宁和诊所后巷的档案室还亮着一盏孤灯。沈之一撬开锈蚀的铁锁,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。空气中弥漫着纸张霉变与消毒水混合的气味。
这里本该在三年前就数字化归档,却因“涉及敏感心理数据”被永久封存。他打着手电,
光束扫过一排排铁柜,最终停在标有“X-07 实验组·绝密”的抽屉上。他抽出文件夹,
封面上贴着五张学生证照片:沈之言、林砚、程雨柔……以及两个已故成员。
程雨柔的照片最旧,边缘被水渍浸染,左耳后的痣在黑白影像中像一粒墨点。翻开第一页,
是她的入组评估报告:沈之一呼吸一滞。他继续翻阅。程雨柔的实验日志显示,
她是唯一一个在“镜像暴露测试”中未出现人格分裂迹象的人。
记录写道:“受试者坚持‘镜子里的人不是我’,即便被催眠三次,仍拒绝认同影像。
异常稳定,或为系统突破关键。”但最后一页,有一行手写批注,墨迹不同,
字迹锋利:沈之一猛地合上文件夹,手心渗汗。
他忽然想起弟弟日记里那句被划掉的话:“雨柔说,她从小就有个姐姐,但从没人见过。
”——那不是姐姐。是另一个她。同一时间,程雨柔蜷缩在出租屋的床角,
怀里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。这是她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。磁带缓缓转动,沙沙的杂音后,
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,颤抖而急促:录音戛然而止。程雨柔盯着墙上的镜子,呼吸渐重。
镜中,她的倒影没有同步。她抬手,镜中人却缓缓摇头。“不……”她后退,撞翻台灯。
镜中人嘴角微扬,无声开口:三天后,心理系旧楼。
沈之一带着打印出的档案复印件找到林砚。对方正站在实验楼天台,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,
像在等待什么。“你早就知道?”沈之一质问,“程雨柔不是测试体,她是容器。
你们在用她复活她母亲的意识?”林砚没有回头,声音平静:“不是复活。是延续。
周临发现,某些高共情个体的大脑,能承载‘断裂的认知’。他称之为‘意识寄生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