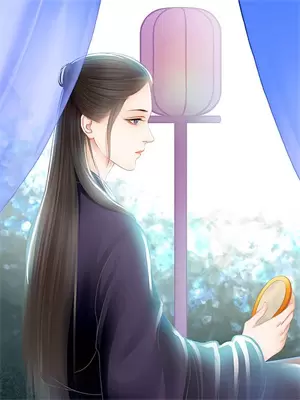暑假被扔到偏远山村外婆家,我本想拍点田园风光应付学校作业。
却发现每夜阁楼传来神秘声响,偷看时发现外婆对着枯井祭拜。村里老人见到我都很惊慌,
说着“太像了”纷纷躲避。直到我在外婆锁着的木箱里,
找到一张民国时期与我长相一模一样的女子照片。背后写着:“井底埋着真相,但别挖开。
”---1七月流火,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轰鸣声差点震碎我的耳膜,
屁股底下的硬木板凳硌得生疼。我垮着脸,抱着我的宝贝单反相机,
看着两旁飞速后退、越来越荒凉的景色,心里把那对迫不及待过二人世界,
把我打包扔到这鸟不拉屎地方的爹妈吐槽了一万遍。“丫头,前面就到咯!
”开拖拉机的黑瘦大叔操着浓重的口音,回头吼了一嗓子,差点把我魂吓飞。
我勉强扯出个笑,举起相机,对着远处连绵的、绿得发黑的山峦按了下快门。“咔嚓”一声,
算是给这次“发配边疆”之旅开了张。村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老旧,
像是被时光遗忘在了某个角落。泥坯房,青石板路,歪歪扭扭的电线杆,唯一鲜亮点的,
是墙上那些褪了色的标语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,有泥土的腥气,有牲畜的粪便味,
还有隐隐的、说不清的植物腐烂的气息。外婆家就在村尾,几乎是最偏僻的一处。
低矮的土墙,黑瓦的屋顶,木门上的铜环都长了厚厚的绿锈。听到动静,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一个穿着藏蓝色布衣、身形干瘦的小脚老太太走了出来。
她脸上皱纹很深,像是用刻刀划上去的,眼神浑浊,看人的时候没什么温度,
只是在我脸上停留了好几秒。“外婆。”我干巴巴地叫了一声。她没应,只是点了点头,
转身就往里走。“屋头有饭,自己热。”得,沟通看来是场硬仗。
我认命地拖着行李箱跟进去,院子倒是挺大,角落里一棵老槐树枝叶虬结,遮天蔽日,
让整个院子都阴凉下来,甚至……有点阴森。院子正中央,赫然有一口用巨石半封住的枯井,
井沿爬满了墨绿色的青苔。我的房间挨着堂屋,隔壁就是个窄小的木梯,通向上面的小阁楼,
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式铜锁挂在阁楼门上。2接下来的几天,我白天就拿着相机在村里晃荡,
拍那些破败的老屋,拍蹲在墙根晒太阳打盹的老人,拍漫山遍野的野花,
琢磨着怎么拼凑出一个“诗意田园”的摄影集,回学校交差。
可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总透着古怪。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在村口那棵大樟树下坐着,
我一靠近,他们交头接耳的声音就停了,一双双浑浊的眼睛齐刷刷地钉在我脸上,先是惊愕,
然后是某种……恐慌?嘴里还念念叨叨。“像,太像了……”“尤其是那双眼睛,
活脱脱……”像谁?我问他们,他们却又像受了惊吓,要么摆着手匆匆走开,
要么就闭紧嘴巴,眼神躲闪。更怪的是夜里。外婆话极少,天一擦黑就回了自己屋子,
整个老宅静得吓人,只有不知名的虫子在角落唧唧。第一晚,大概凌晨一两点,
我正戴着耳机打游戏,一阵极其轻微的、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行的“沙沙”声,
钻进了耳朵。我猛地摘下耳机,屏住呼吸。声音没了。可当我重新戴上,
那声音又隐隐约约传来,断断续续,好像……是从头顶的阁楼传来的?第二天,
第三天……每晚如此。我问外婆阁楼上是不是有老鼠,她正在灶台边生火,头都没抬,
硬邦邦地甩过来一句:“听差了,是风。”风能吹出这种动静?我心里直打鼓。直到昨晚,
那声音格外清晰,还夹杂着极低的、如同梦呓般的絮语。我按捺不住,蹑手蹑脚地爬起床,
赤着脚走到房门边,透过那条细细的门缝往外看。月色很淡,院子里一片朦胧。
只见外婆那瘦小的身影,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那口枯井边。
她穿着一身诡异的、从未见过的深色衣服,有点像……寿衣?手里端着一个破旧的陶碗,
她对着枯井弯下腰,嘴里念念有词,然后把碗里的什么东西,一点点地洒进了井里。那动作,
庄重又透着说不出的邪门。一股寒意瞬间从我的脚底板窜上了天灵盖。她在祭拜?
祭拜一口枯井?3外婆有个上了年头的老木箱,一直放在她床底下,
用一把黄铜锁锁得严严实实。我对里面的东西本来没什么兴趣,但接连几天的怪事,
像猫爪子一样挠着我的心。今天下午,外婆破天荒地说要出去邻村走个远亲,晚上不回来。
这简直是个天赐良机。我在院子里转悠了好几圈,确定她真的走远了,才溜回她的房间。
那口箱子沉甸甸的,锁是老样式,我折腾了半天,用两根细铁丝勉强捅开了锁芯。
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箱盖弹开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。里面大多是些旧衣服,
叠得整整齐齐,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。我胡乱翻了几下,
手指在箱底触到一个硬硬的、方方的东西。摸出来一看,是一个用油布包着的相框。
心跳莫名地快了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,小心翼翼地揭开已经发脆的油布。
相框里嵌着一张黑白照片,边角泛黄,看样子有些年头了,像是民国时期的。
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年轻女子,站在一棵梨花树下,眉眼清秀,带着淡淡的忧郁。
当我看清她的脸时,浑身的血液“嗡”地一下冲上了头顶。
那张脸……那张脸几乎跟我一模一样!一样的眉眼,一样的鼻梁,
连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都分毫不差!唯一的区别,是她的发型,
是那种民国时期常见的学生头,透着一股我没有的文静。我手抖得厉害,几乎拿不稳相框。
翻过来,相框背后没有玻璃,照片背面直接露了出来,
用毛笔写着几行娟秀的小字:“井底埋着真相,但别挖开。”落款是三个字:沈素心。井底?
是院子里那口枯井?真相?什么真相?为什么……别挖开?
巨大的恐惧和强烈的好奇像两条毒蛇,死死地缠住了我的心脏,几乎让我窒息。
照片里这个叫沈素心的女人是谁?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样?她和外婆是什么关系?
井里到底有什么?我猛地想起村里老人见到我时的惊恐,
想起外婆夜半对着枯井的祭拜……所有这些碎片,仿佛都被这根无形的线串了起来,
指向一个深不见底、令人胆寒的秘密。窗外,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,乌云压顶,山雨欲来。
老宅里,只剩下我粗重而混乱的呼吸声。那口幽深的枯井,在渐渐降临的暮色里,
沉默地对着我,仿佛一张准备吞噬一切的巨口。我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将相框塞回油布包,
手忙脚乱地把它按原样塞回箱底,又把那些旧衣服胡乱堆回去。合上箱盖,
铜锁“咔哒”一声扣上,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心脏在胸腔里擂鼓,咚咚咚,
震得耳膜发疼。沈素心。井底。真相。别挖开。这几个字在我脑子里疯狂盘旋,
搅成一团乱麻。外面天色彻底黑透了,狂风卷着豆大的雨点,“噼里啪啦”砸在瓦片上,
像是无数只手在疯狂拍打。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张牙舞爪地摇晃,投影在窗户纸上,
如同鬼影幢幢。外婆不在,这偌大的老宅,只剩下我和……那口井。我把房间门栓死,
后背紧紧抵着冰凉的门板,冷汗浸湿了单薄的夏衣。阁楼上那“沙沙”声又来了,
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清晰,夹杂在风雨声里,像是有东西在缓慢地、坚持不懈地爬行。不,
不是老鼠,那声音更沉,更滞涩。这一夜,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,相机紧紧抱在怀里,
仿佛它能给我一点微不足道的安全感。4雨下了一整夜,天亮时才渐渐停歇,
院子里一片狼藉,断枝落叶铺了满地。那口枯井被雨水浸泡,井沿的青苔显得更加幽深墨绿。
外婆是中午回来的,挎着个篮子,依旧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,
仿佛昨夜她只是去邻居家串了个门。她浑浊的眼睛扫过我苍白的脸,什么也没问。
我强迫自己镇定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,但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那口井,
还有床底下的木箱。外婆在灶间做饭,我状似无意地提起:“外婆,
院里那口井……怎么封上了?都没水用了。”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,刀锋落在砧板上,
发出沉闷的一声。“早就枯了,封了干净。”语气平淡,没有波澜。“哦……”我扒着门框,
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只是好奇,“那……村里人说我跟一个人长得很像,是谁啊?”“哐当!
”外婆手里的菜刀掉在了洗菜盆里,溅起一片水花。她猛地转过头,
那双总是没什么神采的眼睛骤然锐利起来,死死盯着我,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。
“谁跟你胡吣的?!”她的声音又尖又厉,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恐慌和愤怒,
“没事少听那些老糊涂嚼舌根!像什么像!谁也不像!”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反应吓住了,
讷讷地不敢再问。她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,弯腰捡起菜刀,在水盆里用力涮了涮,不再看我,
只是硬邦邦地命令:“吃饭!”接下来的两天,风平浪静。但我能感觉到,
一种无形的、紧绷的东西横亘在我和外婆之间。她看我的眼神里,多了审视,
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……防备。而村里人,似乎也被外婆警告过,见到我更是避之唯恐不及,
连那几句含糊的“太像了”都听不到了。这种刻意的平静,
反而让那股探寻的欲望在我心里疯狂滋长。真相就像一颗种子,一旦破土,就再也无法扼制。
我必须知道,井里到底有什么。沈素心是谁。我为什么和她长得一样。
5机会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降临。外婆被村长叫去商量什么事情,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
我没有任何犹豫,冲进杂物间,找到了一柄生锈但还算结实的铁镐,又拿了一把强光手电筒。
心脏跳得快要冲出喉咙,手心全是汗,黏腻腻地握着镐柄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
只有知了在声嘶力竭地鸣叫。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缝隙洒下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,
那口半封的井沉默地卧在光影中央,像一只沉睡的怪兽。我走到井边,深吸一口气,
举起铁镐,朝着封住井口的那块大青石边缘,用力砸了下去!“铛!
”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,石屑飞溅。巨大的反震力让我手臂发麻。
封石比我想象的还要沉重坚固。我不能放弃,咬着牙,又是一镐,两镐,
三镐……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,又涩又疼,我也顾不上擦。不知道砸了多少下,
只听“咔嚓”一声细微的碎裂声,大青石边缘出现了一道裂缝。我心中一喜,扔掉铁镐,
用尽全身力气去推那块石头。“嘎吱——吱呀——”石头摩擦着,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,
缓缓挪开了一道足够我侧身钻入的缝隙。
一股阴冷、潮湿、带着浓重土腥味和某种难以形容的陈旧气息的风,猛地从井口倒灌出来,
吹得我汗湿的脊背一阵发寒。井口黑洞洞的,深不见底。我打开强光手电,趴在地上,
探头朝里面照去。光线刺破黑暗,笔直地向下延伸。井壁是粗糙的石头垒砌,
布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不知名的黑色污渍。光束一直往下,往下……终于,
在大概七八米深的地方,照到了底。井底并非全是淤泥和碎石。在手电光圈的正中央,
赫然映出了一截惨白惨白的东西。那……那分明是一段人的手骨!五指微微蜷曲,指骨纤细,
静静地躺在黑色的淤泥里。光束颤抖着移动,照亮了手骨旁边——半掩在泥土里的,
是一个小小的、已经氧化变黑的银镯子。以及,
几片早已腐烂、但依稀能看出是深色旗袍的布料碎片!“嗡——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
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照片上的沈素心,穿的就是旗袍!井底埋着的……是她的尸骨?!
那外婆……外婆这些年,夜半祭拜的,
难道就是这井底的……无边的寒意像无数条冰冷的毒蛇,瞬间缠紧了我的四肢百骸。
我猛地向后跌坐在地上,手电筒从脱力的手中滚落,光线在井口乱晃,最终“啪”一声,
熄灭了。我连滚带爬地向后猛退,后背重重撞在冰冷潮湿的井壁上,粗粝的石块硌得生疼,
却远不及心底冒出的寒意。黑暗中,那双井底的枯骨仿佛正透过层层黑暗,无声地凝视着我。
强光手电滚落在脚边,光束斜斜打在老槐树虬结的根部,映出一片晃动的、扭曲的光斑。跑!
必须立刻离开这里!我手脚并用地想从地上爬起来,双腿却软得像煮烂的面条,
根本不听使唤。牙齿不受控制地磕碰,发出“咯咯”的轻响。脑子里乱成一锅粥,
、井底那截惨白的手骨、外婆夜半对着枯井祭拜时佝偻的背影……所有画面疯狂交织、旋转,
几乎要将我的理智撕裂。就在这时,一阵极其轻微的、布料摩擦的“窸窣”声,
从我头顶上方传来。我浑身一僵,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迅速褪去,留下冰冷的麻木。
我一点点,极其缓慢地抬起头。阁楼!那声音来自阁楼!不是老鼠,绝对不是!
那是一种更沉重、更滞涩的……拖行声。伴随着极其微弱的、断断续续的,
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喉咙发出的……呜咽?外婆不在家。这房子里,除了我,还有谁?
或者说……还有什么?“沙沙……沙……”声音在移动,沿着阁楼狭窄的空间,
慢慢挪到了那个通往楼下的、紧锁的木梯口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,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
连呼吸都屏住了。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,死死盯着那扇通往未知恐怖的木梯门。
那把生锈的铜锁,在从门缝透进来的微弱天光下,泛着冰冷的光。它会下来吗?
门后的东西……恐惧像冰冷的藤蔓,一圈圈缠紧我的心脏,越收越紧,几乎要把它勒爆。
我不能待在这里!绝对不能!求生的本能终于压倒了僵直的身体,
我猛地吸进一口带着浓重霉味的空气,手脚并用,几乎是爬着冲回了自己的房间,
“砰”地一声甩上门,手抖得几乎无法将门栓插上。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,
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冷汗已经将全身浸透。外面,阁楼的“沙沙”声和呜咽,不知何时,
悄然停止了。老宅恢复了死寂。但这死寂,比任何声音都更令人胆寒。
7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瘫坐了多久,直到窗外天色开始泛青,黎明将至。
四肢百骸都充斥着一种极度的疲惫和冰冷。真相的碎片似乎就在眼前——沈素心死于非命,
被埋尸井底。外婆知情,甚至可能……参与了掩盖。那阁楼上的,又是什么?
是沈素心无法安息的亡魂?还是别的什么?这里面的水,比我想象的还要深,还要浑浊,
足以将人溺毙。我不能待下去了。必须走,立刻,马上!我挣扎着爬起来,
开始胡乱地将自己的东西塞进行李箱。相机、充电器、几件换洗衣服……动作仓促又慌乱,
东西掉在地上也顾不上捡。必须在天亮前,在外婆回来前离开这个鬼地方!
就在我拉上行李箱拉链,准备一鼓作气冲出去的时候,院门外,传来了脚步声。
不是外婆那种缓慢、拖沓的步子。是几个人的脚步声,沉重而杂乱,
还夹杂着压低的、急促的交谈声。我的心猛地一沉,几乎是扑到窗边,撩起窗帘一角,
小心翼翼地向外窥视。天色微明,薄雾未散。院门外,站着三个人。除了外婆,还有村长,
以及一个我从没见过的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、身形高瘦、眼神锐利得像鹰隼的老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