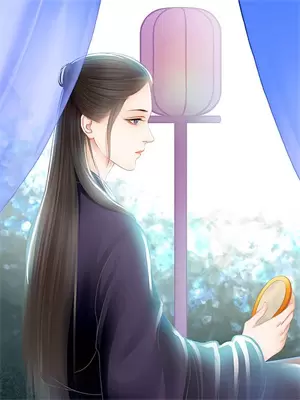1 诡异木马收到爷爷从乡下寄来的那个泛黄的包裹时,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。
敲打着窗玻璃,声音细碎而绵长。像是无数根冰冷的手指在不知疲倦地抓挠。包裹不大,
捧在手里轻飘飘的,拆开来,一些散发着浓重樟脑丸和旧木头柜子气息的零碎。
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烟袋锅,几枚边缘模糊的像章,一本页面焦黄字迹难辨的老黄历。
还有个褪色得厉害的木头马玩具。这木马只有巴掌大小,做工粗糙得可怜,
看得出是手工雕刻的,刀法稚拙,马脖子弯成一个僵硬而诡异的弧度,仿佛被人强行扭过。
四条腿像四根细棍,直挺挺地戳着,勉强维持着站立的姿态。表面的红漆早已斑驳脱落,
露出里面灰白且带着木瘤的底色。马眼睛只是两个随意点上去的黑点,
透着一股子呆滞的死气,多看几眼,心里就莫名地发毛。拿在手里把玩,
指尖立刻传来一种沁入骨髓的冰凉。即使在这阴雨连绵的潮湿天气里,也久久不散。
反而像是能吸走人手上的那点热气。皱了皱眉,心头掠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,
随手把它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,没太当回事。爷爷去世不久,
这大概是他留给我的不多的念想之一。2 禁忌警告这玩意儿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东西。
堂哥阿强是晚上快九点时过来的,头发和肩头都带着屋外带来的湿气,
鞋底在地板上留下淡淡的水痕。他说是刚好在附近办事,顺路过来坐坐。但我看他眼神躲闪,
进门后寒暄两句,视线就不住地往茶几上瞟,多半是听说了爷爷寄东西来,特意过来看看。
我们兄弟俩感情不算特别亲厚,他常年在外地打工,一年见不了几次,但毕竟血浓于水。
母亲给他倒了热茶,他捧在手里,暖了好一会儿,才像是无意中提起似的,
伸手拿起了那个木马,翻来覆去地看,手指反复摩挲着木马冰冷僵硬的脊背,
脸色在节能灯的白光下有些阴晴不定。“这东西……”他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
声音有些发干发涩,“小默,听哥一句,这玩意儿不吉利,还是……还是找个地方扔了吧。
”“干嘛?”我正低头刷着手机,头也没抬,“爷爷的遗物,留个念想罢了。又不占地方,
一个破木头马能有什么不吉利的。”阿强欲言又止,放下茶杯,把木马也放回茶几上。
仿佛那玩意儿突然变得烫手。他凑近了些,压低了声音。
带着一种乡下人讲古时才有的神秘和忌讳“咱们老家……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,夜半三更,
阴气最重的时候,不能看着马眼睛,尤其不能对着黑乎乎的学马叫。”我觉得有些好笑,
抬起头看他:“为什么?怕把狼招来?这城里连个耗子都少见。”这都什么年代了,
还信这些。“比狼邪乎多了。”阿强脸上的肌肉绷紧了,眼神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。
“会引来‘马媳妇’。”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,声音压得极低,
气流像是从齿缝里艰难地挤出来。带着一股子渗入骨髓的寒意。“而且,我听说咱爷的哥哥,
好像就是因为他死的。”“马媳妇?”这名字听着就怪,
透着一股子陈腐的、乡野传说的味道。“嗯,”阿强重重地点了一下头,
眼神里那种复杂的情绪更浓了,像是积年的恐惧,又像是某种无奈的怜悯,还夹杂着点焦躁。
“那东西……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是个啥,老辈子人传的说法也不一样。
有说是以前被马队踩死的可怜女人化的怨灵,有说是山里成了精、专门祸害牲口的邪怪。
反正邪性得很,它要是看见晚上有人盯着他,就会觉得是在召唤它。会顺着声音找上来,
缠上看它的人家,或者……缠上学叫的那个人。”他顿了顿,喉结滚动了一下,补充道,
声音更低了。“它会让你……慢慢地,一点一点地,变得不像你自己。
直到最后……不死不休。”看着他严肃得近乎僵硬的脸,
还有那双因为紧张而微微收缩的瞳孔,心里的不以为然更重了。堂哥以前虽然也信点这些,
但没这么神叨叨啊,出去打了几年工,怎么还把乡下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当真了?
我扯了扯嘴角。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:“得了吧,强哥,吓唬小孩的玩意儿,你也信?
城里没这讲究,楼上楼下邻居隔音差,学狗叫的都有,也没见谁家出事。”阿强看着我,
眼神里那种混合着恐惧和怜悯的情绪几乎要溢出来。他张了张嘴,似乎还想说什么。
但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他没再多费口舌劝我,只是伸手用力抓住我的胳膊,
手指掐得我有些疼。郑重其事地、一字一顿地叮嘱:“小默,哥没骗你!这话你千万记住,
刻在心里!别试!任何时候,任何情况,都别试!就当没听过这回事!
”他像是怕再多待一会。就会惹上什么甩不掉的脏东西似的,猛地松开手,
匆匆起身、3 夜半马嘶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,连我母亲在后面,
留他吃宵夜的喊声都没听见,身影很快消失在楼梯口那片浓稠的黑暗里。
他越是这样神叨叨、如临大敌,我心底那股子被逆反心理,
和好奇心拱起来的火苗就越是蹿得高。什么马媳妇,狗媳妇,故弄玄虚。我偏要试试,
看这玩意儿到底能招来什么。说不定就是个自己吓自己的无聊把戏。晚上,
我熬夜和朋友联机打游戏,激烈的键盘鼠标敲击声和耳机里的喊杀声,暂时驱散了心头,
那点因堂哥警告而带来的微妙不适。直到凌晨三点,才意犹未尽地结束。窗外万籁俱寂,
雨不知何时停了。冷凝的水滴从屋檐边缘断续坠落的“滴答”声,清晰得有些刺耳。
屋子里只剩下电脑风扇停转后的余韵。自己略显粗重的呼吸声。我鬼使神差地走到客厅窗前,
撩开厚重的窗帘一角。外面是沉沉的、化不开的墨色,像一块巨大的黑绒布笼罩着世界。
远处零星的路灯光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反射出破碎而模糊的光斑,
拉出长长短短、扭曲变形的影子。心里带着一丝恶作剧的快意、对自己胆量的证明,
以及一种“打破禁忌”的隐秘兴奋感。我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,眼睛死死的盯住马的眼睛,
然后捏住自己的脖子,尽力模仿着电影里听到的马匹嘶鸣。
“咴咴咴——”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。甚至因为我的刻意模仿,
带着点难听的滑稽和破音,尾音还带着点颤抖。叫声在空旷的楼道里似乎引起空洞的回响,
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回应。叫完,我自己都忍不住低笑了两声,摇摇头,
觉得自己的行为真是无聊透顶。除了远处不知哪栋楼隐约传来几声不满的犬吠,
周围一切如常。窗外的夜色依旧沉静,甚至没有多刮进来一丝风。堂哥的警告,
纯粹是乡下人的迷信,自己吓自己。4 阿强异变我带着对这无聊禁忌彻底的不屑,
关掉电脑,回房睡觉了,一夜无梦,睡得意外沉。第二天,一阵急促得要捶破门板的敲门声,
和母亲带着哭变了调的呼喊惊醒。“小默!小默!快起来!出事了!
阿强……阿强他……”我心头猛地一沉,像是骤然坠入冰窟。
昨晚那点微不足道的得意烟消云散,一种冰冷粘稠的预感像沼泽里的藤蔓,
倏地缠上了我的脊椎,并且不断收紧。“不会吧?”我胡乱套上衣服。母亲站在门外,
脸色惨白如纸,眼圈红肿,浑身抖得像是风中的落叶,见到我,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嘴唇哆嗦着:“快,
他……他在小区里……样子……样子不对……”我跟着母亲跌跌撞撞跑到隔壁单元的婶子家。
院子外面已经围了几个早起锻炼和买菜的邻居,个个面露惊恐。指着院子中央低声议论着,
交头接耳,却没人敢靠近。然后,我看到了阿强。他直挺挺地跪在中央,
那片还没完全干透的泥土地上。面向的,赫然是我家窗口的方向!他低着头,
脖颈以一种极不自然的角度佝偻着,仿佛颈椎已经折断,双手怪异地反剪在身后,
手腕紧紧交叠,像是被无形的绳索死死捆缚着。他的膝盖,竟然深深陷进了松软的泥地里。
周围的地面甚至微微隆起,仿佛不是自己跪下去的。
而是被什么巨大的、来自地底的力量硬生生砸进去、钉在地上的!
最让人头皮发麻、胃里翻腾的是他的嘴。他的嘴唇周围,下巴,
甚至一直延伸到胸前的衣襟上,都沾满被反复嚼得稀烂的草绿色料渣。
那股只有在乡下牲口棚里才能闻到的,混合着青草、唾液和胃酸发酵后的酸腐腥臊气味。
隔着几步远都扑面而来,呛得人几乎窒息。一些未被完全嚼碎的草茎,
不知名的野菜叶子从他微微张开的嘴角溢出来。沾在他灰败毫无血色的脸颊和脖子上,
看上去既恶心又恐怖。“阿强!阿强!我的儿啊……你这是怎么了?!”婶子哭喊着扑上去,
用力摇晃他的肩膀,试图把他从那种诡异的姿态中唤醒。
阿强的身体随着摇晃无力地晃动了几下,像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。然后,他猛地抬起头!
他的眼睛睁得极大,眼白上布满了蛛网般密集的血丝。瞳孔却是一片死寂的空洞,
没有任何焦距,仿佛灵魂已经被某种东西彻底抽走了,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。他咧开嘴,
露出沾满湿漉漉绿色草渍的牙齿,
喉咙深处发出一种类似马匹吃饱后满足时打响鼻的“噗噜噜、噗噜噜”的声音。
那声音带着胸腔的共鸣,绝非人类能轻易模仿,透着一股浓浓的、非人的牲口味。
5 牙齿异化然后,他像是耗尽了所有支撑这诡异姿态的能量。
或者那操控着他的无形力量骤然消失,头一歪,整个人像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,
彻底昏死过去,不省人事。院子里瞬间一片死寂,只剩下婶子撕心裂肺的哭嚎声。
邻居们倒吸冷气。我僵在原地,四肢百骸像是被瞬间冻住,血液都凝固了,
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。凌晨那声愚蠢的、带着挑衅意味的马嘶,此刻像烧红的烙铁,
带着惩罚的炽热,一遍遍狠狠地烫在我的脑海里。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无比,伴随着堂哥昨晚,
那恐惧而严肃到极点的警告,
如同丧钟般轰鸣:“会引来马媳妇……不死不休……”阿强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
一系列的检查下来。医生给出的结论是:生理指标基本正常,除了轻微脱水和电解质紊乱,
找不到任何导致他昏迷和做出如此诡异行为的原因。
脑部CT、血液检查、神经反射……一切看起来都“没问题”。
对于他满嘴的草料和那深入泥地的跪姿,医生也只能困惑地摇头,表示无法用现代医学解释,
最后含糊地归结为“罕见的癔症或应激反应”。只有我知道,那声马叫之后,禁忌被触犯了,
某种不该存在于这个现代都市,阴冷邪门的东西。循着那声愚蠢的嘶鸣,找上门来了。
“马媳妇”……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,它是真的!而且,它似乎……认错了人?或者,
它迁怒于警告过我的人?阿强住院观察,婶子留在医院照顾他。浑浑噩噩地回到家,
巨大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,反复冲刷着我,让我坐立难安。
不敢告诉任何人我那晚的愚蠢行为,包括几乎崩溃的婶子和满心疑惑的父母。
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拉上厚厚的窗帘。
试图用“阿强可能是梦游或者不小心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”这类苍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。
但心底深处清楚地知道,祸是我闯下的。那恐惧黏稠得如同沥青,缠绕住我的心脏,
挤压着我的肺叶。让我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濒临窒息的恐慌。
我试图用疯狂的工作和沉浸式的游戏来麻痹自己。但阿强跪在院子里,满嘴草料,
眼神空洞地打响鼻的画面,总在我眼前晃动,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