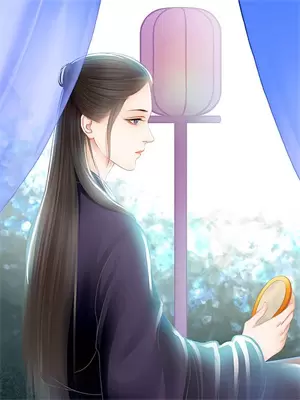天地间只剩下白。这白不是纯净的雪色,而是浑浊的、粘稠的,
仿佛将整个世界的陈年污垢都熬煮成了蒸汽,翻滚着,弥漫着,吞噬了一切。
山峦、树木、崎岖的土路,尽数消失了踪影。陆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,
脚下的泥泞像是无数只冰冷的手,死死攥着他的鞋底,每一次抬脚都耗费着所剩无几的力气。
他是个古董贩子,靠着眼力和腿脚吃饭,常年游走在荒僻之地,从蒙尘的旧物里淘换生计。
这次听闻这片大山深处偶有品相极佳的青铜小件流出,便循着模糊的线索一头扎了进来。
却没承想,撞上了这百年不遇的浓雾。指南针早已失灵,指针疯了一样乱转。
手机更是成了块冰冷的板砖,一丝信号也无。汗水混着雾水浸透了内里的衣衫,
冰冷地贴在皮肤上。他抹了把脸,手掌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汗是雾。呼吸变得艰难,
那白濛濛的雾气仿佛带着分量,压在他的胸口。“鬼天气……”他低声咒骂了一句,
声音出口便被浓雾吸收,传不出多远就消散了。心头那点因职业而生的敏锐直觉,
此刻像根被拨动的琴弦,微微震颤着。这雾,邪性。不单单是浓,
更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,像是……铁锈混杂着陈腐的霉味,若有若无地往鼻子里钻。
他停下来,努力睁大眼睛向四周望去,依旧是那片无边无际的白。寂静,死一般的寂静,
连惯常的山野虫鸣都听不到一丝。整个世界仿佛被这巨大的、活物般的雾气给消化了。
不能再走了。陆明很清楚,在这种环境下,盲目移动只会加速消耗体力,
甚至可能失足跌落山崖。他靠着一棵形状扭曲、树皮湿滑的老树,喘着气,心里盘算着对策。
就在绝望渐渐漫上心头时,一阵极轻微、仿佛隔着好几层棉布的声音,飘进了他的耳朵。
是铃铛声。不是清越悦耳的那种,而是极其沉闷,短促,咚…咚…咚…,
像是用裹了厚布的槌子,敲击着生锈的铁片。声音断断续续,却带着某种固定的节奏,
穿透浓雾,指引着一个方向。陆明精神一振。有声音,就意味着有人烟。
他顾不上细想这铃声的怪异,求生本能催动着他,循着那微弱得几乎要被心跳掩盖的声响,
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。雾气似乎薄了一些,影影绰绰地,前方出现了模糊的轮廓。随着靠近,
轮廓逐渐清晰,那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木屋,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,
如同从山体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瘿瘤。村口立着一座歪斜的牌楼,木质腐朽,
上面的字迹早已剥落模糊,难以辨认。铃声是从村子深处传来的。陆明迈步走进村庄。
脚下的路变成了坑洼不平的碎石和泥土混合体,两侧的房屋门窗紧闭,悄无声息。
屋檐下挂着一些晒干的、叫不出名字的野菜,颜色暗沉。整个村子静得可怕,
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墓。只有那沉闷的铃声,依旧固执地响着,来源似乎是村子中央某处。
他沿着狭窄的、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往里走,目光警惕地扫过两侧。一扇虚掩的木门后,
似乎有黑影一闪而过。他猛地转头,却只看到门内深沉的黑暗。“谁?”他试探着问了一句。
没有回应。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死寂的巷道里碰撞,带回空洞的回音。终于,
在村子中央一小片算是广场的空地上,他看到了铃声的来源。
一个穿着臫黑色粗布衣服、身形佝偻的老者,背对着他,手里提着一盏昏黄的油灯,
另一只手正机械地摇晃着一个巴掌大的、色泽暗沉的青铜铃铛。那沉闷的声响,
正是由此发出。老者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,缓缓转过身来。油灯的光晕映照出他的脸,
布满刀刻般的皱纹,一双眼睛浑浊不堪,几乎看不到眼白,只有两个深不见底的黑点。
他直勾勾地看着陆明这个不速之客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既无惊讶,也无警惕。“外乡人?
”老者的声音干涩沙哑,像是两块粗糙的石头在摩擦。陆明赶紧挤出一丝笑容,
上前拱了拱手:“老人家,我是过路的,遇上这大雾迷了方向,想在贵宝地借宿一晚,
不知可否行个方便?”他刻意放缓语速,让自己显得诚恳而无害。老者沉默着,
那双黑洞般的眼睛在陆明身上停留了许久,久到陆明几乎以为他不会再开口。
周围的雾气似乎更浓了,将这片小广场紧紧包裹,只有老者手中的油灯,
散发出一点微弱而固执的光晕。“跟我来。”最终,老者吐出三个字,转过身,
不再摇晃铃铛,只是提着灯,迈着蹒跚的步子朝广场一侧走去。那铃声一停,
整个村子仿佛陷入了更深的死寂,连空气都凝固了。陆明不敢怠慢,连忙跟上。
老者带着他来到广场边缘一栋相对齐整些的二层木屋前。木屋的门廊下,
挂着一串风干的兽骨,形状奇特,陆明从未见过。“村长。”老者站在门口,低声唤道。
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一道缝,一张同样布满皱纹、但眼神略显清明的脸探了出来。
他看了看老者,又看了看陆明,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“雾瘴起了,外面不安全。
”提灯的老者说完这句,便不再言语,提着灯,身影缓缓没入旁边的雾气中,消失了。
被称为村长的男人上下打量着陆明,目光锐利,带着审视的意味。“外来的?”他问,
声音低沉。“是,迷路了,想借宿一晚,必有酬谢。”陆明再次说明来意,
并从随身的包袱里摸出一个小银锭,递了过去。这是他惯用的手段,钱财开道,
往往能省去不少麻烦。村长瞥了一眼银锭,并没有立刻去接,而是沉吟了片刻,
才侧身让开门:“进来吧。雾散之前,不要出门。”陆明道了谢,迈步走进屋内。
一股混合着烟火、草药和某种淡淡腥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屋里的陈设极为简单,
甚至可以说是简陋,中央是一个火塘,里面的柴火噼啪燃烧着,驱散着屋外的湿寒。
“楼上左边那间空着,你自己去。”村长指了指通往二楼的木质楼梯,语气平淡,
听不出什么情绪,“晚上听到任何动静,都不要出来看,切记。”陆明点头应下,
心中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。这村子,从雾气到村民,都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诡异。
他顺着吱嘎作响的楼梯走上二楼。二楼只有两个房间,他推开左边那间的木门,
一股灰尘味涌出。房间里只有一张铺着干草的木板床,一张歪腿的木桌,窗户用木条钉死了,
只留下几条缝隙。放下行李,陆明走到窗边,透过缝隙向外望去。外面依旧是白茫茫一片,
只能隐约看到对面房屋黑黢黢的轮廓。寂静,还是死一样的寂静。他靠在墙边,整理着思绪。
青铜铃铛……那个老者手里的,还有传闻中流落出去的青铜小件,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?
这诡异的雾气,村民讳莫如深的态度,村长那句警告……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。
不知过了多久,楼下传来轻微的响动,似乎是村长出门了。陆明心中一动,机会来了。
他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村子,关于那些青铜器的事情。他轻轻拉开房门,
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。一楼果然空无一人,火塘里的火也小了许多。
他的目标是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线索,比如村长的物品,
或者听听其他村民的谈话——如果这个村子还有其他人正常活动的话。
就在他经过通往屋后的小门时,旁边堆放杂物的阴影里,突然伸出一只手,
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!陆明浑身一僵,差点叫出声来。他猛地转头,
对上一双在黑暗中显得异常明亮的眼睛。那是一个年轻女子,大约十七八岁年纪,
皮肤是久不见日光的苍白,五官清秀,但眉眼间笼罩着一层浓得化不开的忧郁和惊惶。
她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粗布衣服,身形瘦弱。“外乡人?”女子压低声音,语速极快,
带着颤抖,“你不该来的!趁着雾还没吃人,快走!”“吃人?”陆明心头一跳,
反手握住女子的手腕,感觉到她冰凉皮肤下剧烈的脉搏,“什么意思?这雾到底怎么回事?
”女子紧张地回头望了一眼,生怕有人发现。“雾瘴……雾瘴一起,就会有人……有人发疯!
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,“我姐姐……我姐姐就是上个雾夜……”她的话没能说完,
远处似乎传来了什么声响。女子脸色骤变,猛地甩开陆明的手,
将他往楼梯方向推了一把:“回去!躲起来!记住,无论听到什么,看到什么,都不要出来!
不要相信他们!”说完,她像受惊的兔子一样,迅速缩回了杂物堆后的阴影里,消失不见。
陆明的心脏怦怦直跳,血液冲上头顶。发疯?雾夜?村长的女儿?姐姐的惨死?
信息碎片一股脑涌来,非但没有解开谜团,反而让这诡异的村庄显得更加危机四伏。
他不敢停留,迅速退回二楼房间,关紧房门,背靠着冰冷的木板,大口喘着气。窗外的雾气,
似乎更加浓郁了,那白,不再是单纯的浑浊,而仿佛带着某种活物的恶意,无声地蠕动,
挤压着这栋小小的木屋。夜,还很长。而那沉闷的、令人心悸的青铜铃声,不知何时,
又会再次响起。陆明背靠着冰冷的门板,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撞击,耳畔嗡嗡作响。
楼下那短暂而惊悚的遭遇,像一块冰滑入了他的脊椎,寒意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。
村长的女儿……阿娣。她那双盛满惊恐和绝望的眼睛,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“雾瘴吃人”,
“姐姐就是上个雾夜……”,“不要相信他们”……这些碎片化的警告,
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思绪,让这间本就压抑的斗室,空气都变得稀薄而危险。
他缓缓滑坐在地上,耳朵紧贴着门板,凝神细听。楼下没有任何动静,村长似乎还没有回来。
整个木屋,不,是整个村庄,都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。窗外的雾气更浓了,
透过木板的缝隙,只能看到一片沉滞的、仿佛具有实体的白,连对面房屋的轮廓都已吞噬。
“发疯……”陆明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。什么样的“发疯”,
会让一个年轻女子用那样恐惧到极点的语气描述?联想到进村时那提灯老者麻木空洞的眼神,
那沉闷如同丧钟的青铜铃声,还有村长那句不容置疑的警告……这一切,
都指向某种超出他理解范围的、深植于这个村庄内部的恐怖。他不能坐以待毙。
古董贩子的生涯赋予他的,除了辨识旧物的眼力,更有在陌生险境中寻求生机的本能。
恐惧固然存在,但被蒙在鼓里的未知,往往比已知的危险更致命。时间在死寂中缓慢流淌。
陆明靠在门边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调整呼吸。他需要信息,需要弄清楚这个村庄,
这场大雾,以及那些青铜铃铛背后隐藏的秘密。阿娣是关键,但她显然处于极度的恐惧中,
贸然接触可能会给她和自己都带来灭顶之灾。不知过了多久,也许是一个小时,也许是两个,
楼下终于传来了轻微的响动。是脚步声,很轻,带着一种刻意的谨慎。不是村长沉重的步伐。
陆明的心提了起来。他轻轻挪动身体,将眼睛凑近门板上一道细微的裂缝。是阿娣。
她端着一个粗陶碗,里面似乎盛着些糊状的食物,正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。
她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苍白,眼神慌乱地扫视着四周,像是在躲避什么。
她走到陆明门前,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犹豫。最终,她轻轻将陶碗放在门口的地上,
用手指极快地、几乎不发出声音地叩了两下门板,然后像受惊的鸟儿一样,迅速转身下楼,
消失在视野里。陆明等待了片刻,确认外面再无动静,才轻轻拉开房门,将陶碗端了进来。
碗里是某种混合了野菜和粗粮的糊糊,气味并不好闻,但他此刻也顾不上许多。填饱肚子,
保持体力,才是活下去的前提。他一边机械地吞咽着那寡淡粗糙的食物,
一边思考着下一步行动。阿娣的举动表明她愿意沟通,但受到极大的限制。村长去了哪里?
那些村民呢?这死寂的村庄,活人仿佛都消失了,只剩下这无孔不入、令人心烦意乱的雾气。
夜色渐深,窗缝外透入的光线彻底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黑暗,
只有雾气本身似乎散发着一种极其微弱的、病态的灰白荧光,反而让黑暗显得更加扭曲怪异。
就在陆明以为这个夜晚将在这种紧绷的死寂中度过时,一种新的声音,
毫无征兆地刺破了寂静。不是青铜铃声。而是……脚步声。很多人的脚步声。
它们从村庄的各个方向传来,沉重,拖沓,仿佛穿着湿透的鞋子在泥地里跋涉。脚步声杂乱,
却又隐隐朝着同一个方向汇聚——村子深处,那沉闷铃声曾经响起的方向。
陆明猛地从地上站起,再次凑到门缝边。他看不到具体的情形,
但那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密集的脚步声,像是一支沉默的军队正在黑暗中集结。没有交谈,
没有咳嗽,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到,只有那黏腻而规律的踏步声,敲打着耳膜,
也敲打着他本就紧绷的神经。村长的话在耳边回响:“晚上听到任何动静,都不要出来看。
”阿娣的警告也同时浮现:“不要出来!不要相信他们!”强烈的冲动驱使着他,
好奇心与恐惧交织,几乎要冲破理智的堤坝。他知道危险,
但古董贩子骨子里对“异常”和“秘密”的探究欲,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。他深吸一口气,
做出了决定。极其缓慢地,他将房门拉开一道仅容他侧身挤出的缝隙。楼道里一片漆黑,
只有楼下火塘里残余的几点火星,提供着微不足道的光亮。脚步声正经过楼下,
朝着村后而去。陆明屏住呼吸,像幽灵一样滑出房间,蹑手蹑脚地移动到楼梯口,伏低身体,
向下望去。借着那微弱的、摇曳的火光,他看到了令他头皮发麻的一幕。一个个村民,
男女都有,大多穿着和提灯老者类似的黑色或深色粗布衣服,
排成不算整齐但方向一致的队伍,正沉默地穿过一楼,走向屋后。他们的动作僵硬,
步伐一致,如同被无形的丝线操控的木偶。
最让陆明感到寒意的是他们的脸——没有任何表情,眼神空洞,直视前方,
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,包括趴在楼梯上窥视的他。他们就像……就像失去了灵魂的躯壳,
在执行某种既定的、麻木的仪式。队伍不算长,大约二三十人,很快便走了过去。
脚步声向着屋后延伸,逐渐远去。陆明的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。他知道自己必须跟上。
这诡异的夜行,很可能与阿娣所说的“发疯”,与那神秘的青铜铃铛直接相关。
他等待了片刻,确认再无人经过,才如同狸猫一般溜下楼梯,避开火塘的光亮区域,
闪身来到屋后的小门边。门虚掩着,外面是更浓的黑暗和雾气。他侧身钻出,
冰冷的、带着浓重湿气和铁锈味的空气瞬间包裹了他。他打了个寒颤,
努力适应着外面的黑暗。好在那些村民行走时发出的脚步声,在死寂的夜里如同指路的航标。
陆明保持着距离,借助房屋和杂物的阴影,小心翼翼地尾随着。雾气成了他最好的掩护,
但也阻碍了他的视线,他必须靠得很近才能勉强看清前方模糊晃动的黑影。
队伍并没有在村庄里停留,而是径直穿过了那些破败的屋舍,
朝着村庄后方一座低矮的山坡走去。越往村后走,
空气中的那股铁锈混杂腐败的气息就越发浓烈,几乎令人作呕。
村民们的脚步踏在湿润的泥土和碎石上,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,
在这诡异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。他们沉默地前行,没有人回头,没有人交谈,
只有一种被集体催眠般的麻木。终于,队伍在山坡脚下停了下来。
陆明躲在一块巨大的、生满青苔的岩石后面,小心地探出头。山坡的底部,赫然有一个洞口。
那洞口约一人多高,边缘粗糙不规则,像是天然形成,又带着些许人工开凿的痕迹。
洞口黑黢黢的,仿佛一张择人而噬的巨口,向外散发着比周围空气更阴冷、更污浊的气息。
那股浓烈的铁锈腥味,正是从这里涌出。村民们沉默地聚集在洞口前,依旧排着松散的队伍,
面朝洞穴,一动不动。他们要进去?陆明心中惊疑。这洞穴里有什么?就在这时,
一个佝偻的身影从村民中走出,来到洞口前。借着雾气微弱的反光,陆明认出,
正是傍晚时那个提灯摇铃的老者。他手中依旧提着那盏油灯,
昏黄的光晕在浓雾和黑暗中摇曳,勉强照亮他身前一小片区域。老者面向洞穴,
缓缓举起了手中的油灯,另一只空着的手,则伸向了怀中。陆明屏住了呼吸,
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。老者从怀里掏出的,正是那个色泽暗沉的青铜铃铛。他没有摇晃它,
只是将其托在掌心,高高举起,对着漆黑的洞穴深处。然后,他开口了。
发出的却不是陆明能理解的任何语言,而是一种极其古怪、扭曲的音节。声音干涩嘶哑,
时高时低,断断续续,像是在念诵某种古老而邪恶的咒语,
又像是在与洞穴深处的某种存在进行着沟通。这诡异的吟诵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,
与那浓稠的雾气混合在一起,产生了一种令人心智摇荡的怪异效果。
陆明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,胃里也开始翻腾不适。吟诵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。期间,
洞口的村民们依旧如同石雕,没有任何反应。当最后一个扭曲的音节落下,
老者缓缓放下了铃铛。他转过身,面向沉默的村民,用一种毫无起伏的语调,
陆明视线后的第一句他能听懂的话:“时候到了……进去……聆听‘神谕’……”“神谕”?
陆明心中一凛。这诡异的洞穴,散发着不祥气息的青铜铃铛,麻木的村民,
竟然被称为“神谕”?村民们动了。他们依旧沉默着,但队伍开始向前移动,一个接一个,
迈着那种僵硬而拖沓的步伐,鱼贯而入,走进了那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漆黑洞穴,
身影迅速被黑暗吞噬。老者提着油灯,站在洞口,如同一个沉默的看守,
目送着最后一个村民消失在洞穴深处。陆明藏在岩石后,浑身冰冷。
他亲眼目睹了这超乎想象的一幕。这些村民深夜聚集,进入这个怪异的洞穴,
所谓的“聆听神谕”,究竟是什么意思?阿娣的姐姐,是否也曾是这沉默队伍中的一员,
并在某个雾夜之后,再也没能出来?疑问和恐惧如同藤蔓般缠绕着他。他知道,
洞穴里一定隐藏着这个村庄最核心、最恐怖的秘密。或许,
也包括那些流落出去的青铜小件的来源。他不能进去。直觉,以及阿娣的警告,
都在疯狂地提醒他,踏入那个洞穴,将是万劫不复。他必须离开这里,
回到那间临时的庇护所。在弄清楚更多之前,暴露自己是最愚蠢的行为。
就在他准备悄然后退,沿着原路返回时,站在洞口的老者,那浑浊的、如同黑洞般的眼睛,
似乎……似乎极其缓慢地,朝着他藏身的方向,转动了一下。陆明的血液瞬间冻结了。
是错觉吗?是因为过度紧张而产生的幻觉?还是……那个老者,真的发现了他?他僵在原地,
一动不敢动,连呼吸都停滞了。冷汗顺着额角滑落,滴进衣领,带来一阵冰凉的触感。
老者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。他只是维持着那个姿势片刻,然后缓缓转过身,提着油灯,
也步入了漆黑的洞穴之中。洞口,只剩下无尽的黑暗,
以及那不断从中涌出的、带着铁锈和腐败气味的冰冷空气。陆明又等待了许久,
直到确认洞口再无动静,才敢一点点挪动几乎麻木的身体。他不敢再看那洞穴一眼,
用尽全身的力气,控制着发软的双腿,沿着来时的路,跌跌撞撞地往回跑。
浓雾依旧包裹着他,仿佛有生命的实体,在他身后无声地蠕动、追逐。
回到村长家木屋的过程,像是一场噩梦。他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上二楼,冲进房间,
反手将门栓死死插上,背靠着门板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冷汗已经浸透了内外衣衫。窗外,
那沉滞的、病态的灰白雾气,仿佛无数只窥视的眼睛。而村庄深处,
那吞噬了所有村民的洞穴,此刻正沉默地潜伏在夜色与浓雾之中,像一个巨大而危险的秘密,
刚刚向他掀开了冰山一角。夜,还远未结束。他知道,
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个远比迷路和借宿更可怕万分的漩涡中心。陆明背靠着冰冷的门板,
滑坐在地上,汗水如同小溪般从额角淌下,浸湿了衣领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,
几乎要撞碎肋骨。黑暗中,他大口喘息,
试图将肺里那带着铁锈和腐败气息的冰冷空气挤压出去,却只觉得那味道如同活物,
顽固地盘踞在鼻腔深处,甚至带着一丝…甜腥。
洞穴前的景象在他脑中反复上演:麻木沉默的村民,佝偻老者诡异的吟诵,还有最后,
那双似乎穿透雾气与岩石阻隔、落在他藏身之处的、浑浊如黑洞的眼睛。是错觉吗?
那冰冷的、非人的一瞥,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战栗。
“不要相信他们……”阿娣颤抖的声音再次回响。他们?是指所有村民,包括她的父亲村长?
所谓的“神谕”又是什么?那些进入洞穴的人,在里面做什么?仅仅是“聆听”?
疑问和恐惧像藤蔓一样绞紧了他的思维。他不能坐以待毙。那个洞穴,那些青铜铃铛,
是这一切诡异的核心。他必须知道里面有什么,
哪怕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境地,以及…该如何逃脱。天色微明,
但雾气并未散去,只是从深夜那沉滞的、仿佛具有实体的黑暗,
变成了灰蒙蒙的、弥散的白昼。光线透过木窗的缝隙,
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几道微弱的光斑。楼下传来了动静,
是村长沉重的脚步声和一些碗碟碰撞的轻响。陆明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整理好表情和衣物,
深吸一口气,拉开房门走下楼梯。村长正坐在火塘边,端着一个粗陶碗喝着什么。
看到陆明下来,他抬起眼皮,目光依旧锐利而审视。“昨晚睡得可好?”村长的声音平淡,
听不出任何异样。陆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:“还好,就是这雾气太重,有些气闷。
老人家,这雾通常要多久才散?”“该散的时候自然就散了。”村长呷了一口碗里的糊状物,
语气没有任何波澜,“雾瘴期间,不要乱走。”又是这句警告。陆明点点头,
装作不经意地问道:“昨晚似乎听到些脚步声,还挺多人,是村里有什么急事吗?
”村长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,随即恢复自然,他将陶碗放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