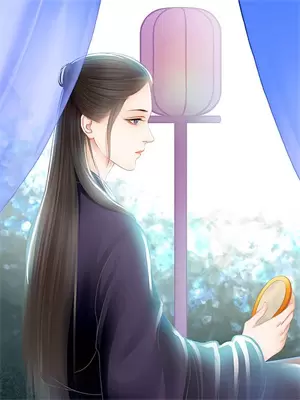1 血色入峡1969年,霜降。天地间的寒气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拧了一把,骤然收紧。
沅水边那条不知岁月的麻石路,在夕阳残照下,泛出一种不祥的、黏稠的血色光泽,
宛如刚被剥开、还滴着温热液体的狐狸皮,铺陈在湘西莽莽苍苍的群山里。
知青办的干部嗓音嘶哑,念完了最后一批名单,像是完成了一项沉重的仪式。
十九岁的北京学生沈卫国,背着半旧不新的铺盖卷,踩着这血色的光,
一步步踏入了湘西最幽深、最神秘的峡谷——落梅峡。他的名字带着时代的烙印,
人却带着一股不属于这里的、来自城市的棱角与傲气。峡谷入口处,
一块被风雨侵蚀得发黑的木牌孤零零地立着,上面用烧焦的木炭,
歪歪扭扭地划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:“夜不赶路。”那字迹潦草,
带着一种近乎仓皇的警告意味。沈卫国停下脚步,嘴角扯起一个混合着轻蔑与不信的弧度。
在他看来,这不过是山里人故弄玄虚,阻碍他们这些“外来者”的伎俩。他伸出手,
握住木牌,用力一拔,将它从湿软的泥土中拔了出来,然后反手,“噗”地一声,
将它倒插进地里,木牌尖锐的底端深深没入泥中,
像插下了一面象征征服与无知的、幼稚的胜利旗帜。
他深吸一口混合着腐叶与湿土气息的空气,迈步深入峡谷的阴影。他没想到,仅仅三个月后,
他会用比木炭更绝望、更猩红的液体,将这四个字,一笔一划,亲手写回这片土地,
字字泣血。2 影随身行与沈卫国同行的,是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叶知秋。她人如其名,
带着南方水乡浸润出的温婉秀气,一双眼睛像是被秋水长久浸泡过的黑李子,清澈,
却总氤氲着一层挥之不去的、湿漉漉的潮气,仿佛藏着无尽的心事。夜里,
临时安置点的茅屋里,一盏煤油灯摇曳着豆大的光芒,将人影扭曲地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。
叶知秋蜷在角落,膝盖上垫着信纸,偷偷给远在上海的母亲写信。
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移动,写到家门口的石库门,写到弄堂里飘起的炊烟,
写到对未来的茫然……笔尖停顿,悬在“沈卫国”三个字上方。墨汁从笔尖渗出,缓缓晕开,
在信纸上泅出一小朵不规则的黑梅,像是某种不祥的印记。她抬起头,
飞快地瞥了一眼不远处正在整理铺盖的沈卫国,随即像是被烫到一般收回目光,
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则地跳动。有些事,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。来的路上,
那列喘着粗气、穿行在无尽山峦间的绿皮火车,在一个幽深的隧道口短暂停顿。
就在列车驶入黑暗前的一刹那,叶知秋无意间望向车窗外。隧道口,
站着一个穿着陈旧褪色嫁衣的女人,那嫁衣红得刺眼,却又蒙着一层死亡的灰败。
女人缓缓抬起手,朝她的方向招了一下。最让叶知秋血液冻结的是,
那女人的脸——破碎不堪,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裂痕,像是一面被石头狠狠砸过的镜子,
拼凑不出完整的五官,只有无尽的空洞与怨毒。火车轰鸣着驶入隧道,黑暗吞噬了一切。
自那天起,叶知秋就感觉自己的影子里,似乎藏了另一个人。光线好的时候,
她能清晰地看到,自己那道本应轮廓分明的影子旁边,或身后,
总是拖着一道极淡、极模糊的虚影,像一条沉默而固执的尾巴,无论她走到哪里,
都如影随形,甩不脱,挣不掉。3 哑铃摄魂公社的安置点,
设在峡谷深处一座废弃已久的“赶尸庙”里。庙宇早已破败,神像不知去向,
只留下空荡荡的殿宇和森然的回忆。公社将其改建成了临时仓库,堆放些农具和杂物。
庙堂很高,光线昏暗,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灰尘和木头腐朽的气味。最引人注目的,
是那根粗壮的主梁,以及梁上悬着的一面布满绿锈的古老铜铃。铃铛不小,样式古朴,
上面刻着难以辨认的符文。奇怪的是,它的铃舌被一根粗硬的铁丝死死绞住,
固定在一旁的梁架上。老保管员是个干瘦的本地老头,眼皮耷拉着,说话慢吞吞。
他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介绍:“这铃,以前是赶尸人用的‘摄魂铃’。讲究着呢,
铃声一响,亡人自己站起来,跟着走,翻山越岭,不敢回头。”沈卫国好奇心起,
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,踮起脚,用力敲向那铜铃。
“铛——”预想中的清越铃声并未出现,只发出一声沉闷、嘶哑的“咔”声,
像是被扼住喉咙的垂死鸟雀发出的最后哀鸣,难听而压抑。“别乱敲!
”老保管员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惧,连忙制止。就在这时,
一直安静站在门口的叶知秋忽然猛地回过头,脸色煞白,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房梁上的铜铃,
声音带着细微的颤抖:“它……它刚才叫我名字。”沈卫国失笑,
觉得她太过敏感:“瞎说什么,风刮的吧?别自己吓自己。”他话虽如此,
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地上的影子上。煤油灯的光线下,叶知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
而那道一直跟随她的淡影,此刻竟像是活了过来,悄无声息地顺着墙壁向上蔓延,
最终与房梁上那面冰冷的铜铃影子贴合在一起,紧密得宛如一块正被阴风风干的人皮。
一股寒意悄然爬上沈卫国的脊背。4 洞神娶亲十月底,峡谷里尚未完全适应知青们的到来,
第一件怪事便不期而至。山脚下苗寨里最强壮的一头水牛,在夜里无声无息地死了。
清晨被发现时,庞大的躯体只剩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牛皮,松松垮垮地蒙在骨架之上,
内脏、肌肉消失得一干二净,空荡得像一个被吹鼓起来、等待放飞的巨大风筝。诡异的是,
牛的两只眼珠子却完好无损,被端正地摆放在牛头骨的前方,
空洞的瞳仁齐刷刷地朝向天边那轮尚未沉落的残月,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“凝视”。
公社书记老覃,一个面色黝黑、总是皱着眉头的中年男人,在社员大会上,
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将死因定性为“豹子掏的”。但他那闪烁的眼神和刻意加重的语气,
并不能服众。散会后,老覃私下叫来了民兵排长阿桑。阿桑是个精悍的苗族青年,眼神锐利,
皮肤是常年山间劳作晒成的古铜色。老覃低声吩咐了几句,阿桑沉默地点点头,
随后便带着沈卫国和叶知秋,走向了峡谷最深处、那个被当地人视为禁忌的地方——落花洞。
落花洞位于峡谷的咽喉之地,洞口被成千上万条垂落的藤蔓遮蔽,那些藤蔓粗壮如儿臂,
色泽深黑,在山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,像极了女人披散下来、永无梳理之日的长发,
散发着阴森的死气。站在离洞口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,阿桑停住脚步,
用低沉的苗语快速念叨了几句,然后转向沈卫国和叶知秋,
用生硬的汉语解释道:“洞神……要娶老婆。被选中的女子,就是‘落花洞女’。
”他指了指那幽深的洞口,“她们得先‘落’进洞里,再像花一样……‘开’出来。
出来的时候,人就已经空了,魂被洞神收走,只剩下一具会笑的空壳子。
”沈卫国听得半懂不懂,眉头紧锁,
试图用他所知的“科学”和“唯物主义”来理解这荒诞的传说。
当他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叶知秋时,心里猛地一沉。叶知秋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,白得吓人,
泛着一种类似青瓷的、被月光反复漂洗过的死青色,嘴唇微微翕动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5 月下聘礼怪事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,接踵而至。叶知秋开始梦游。
第一次发现是在一个霜华浓重的深夜。沈卫国被窗外细微的响动惊醒,起身查看,
赫然看见叶知秋只穿着单薄的衬衣,赤着双脚,像一抹游魂般站在院子中央冰冷的霜地上。
她双手捧着一把不知从何处拾来的、早已枯萎腐败的落花,眼神空洞地望着虚空,
嘴里轻轻哼唱着江南小调《茉莉花》。然而,那原本婉转的曲调,从她唇间溢出时,
却变得扭曲、诡异,拖长的尾音和起伏的腔调,分明是湘西深山裡送葬时才唱的丧歌!
“知秋!”沈卫国心脏骤缩,冲过去一把抱住她冰凉的身体。叶知秋缓缓睁开眼,
瞳孔里没有焦距,反而清晰地倒映出两个月亮的光影——一个明亮,
高悬天际;另一个却晦暗不明,仿佛深藏在某个幽邃的洞穴之底。她看着沈卫国,嘴唇翕动,
吐出的话语冰冷得不带一丝人气:“洞神……给我下聘了。
聘礼是七条牛……还差一条……”她的声音顿了顿,瞳孔中那轮暗月似乎骤然放大,
“用你凑。”一股混杂着恐惧、愤怒和难以置信的情绪直冲沈卫国的头顶,他想也没想,
抬手“啪”地给了她一记耳光,试图将她打醒。叶知秋挨了打,却没有哭闹,也没有清醒,
反而像是被瞬间抽掉了全身的骨头,软软地瘫倒在他怀里,呼吸微弱,口鼻间呼出的气息,
带着一种奇异的、腐烂桃花浸泡在尸水中般的甜腻气味。6 血铃印沈卫国不敢耽搁,
背起意识模糊的叶知秋,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公社唯一的赤脚医生。
那是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老先生,他把手指搭在叶知秋纤细的手腕上,凝神诊了许久,
眉头越皱越紧,最后摇了摇头,摘下眼镜,疲惫地揉了揉鼻梁。“怪,真怪。”他喃喃道,
“这脉象……是双脉。一条是她的,虽弱,还在跳。可另一条……是空的,死沉死沉,
像是在替一个不存在的人把脉。”希望破灭,沈卫国只能将叶知秋带回赶尸庙仓库。夜里,
他不敢合眼,用厚厚的棉被将叶知秋紧紧裹住,又用麻绳小心地捆了几道,
将她束缚在床板上,做成一个无奈的“茧”。子夜时分,万籁俱寂。突然,
房梁上那面被铁丝绞住舌头的铜铃,毫无征兆地自己响了起来!“当——!”声音不再嘶哑,
而是变得清晰、尖锐,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冰冷,在死寂的庙堂里轰然炸响。
梁上积年的灰尘被声波震得簌簌落下,像一场突如其来、带着霉味的阴间小雪。
几乎在铃声响起的同时,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叶知秋,猛地直挺挺坐起!她的眼睛依旧紧闭,
嘴角却以一种人类无法做到的幅度,猛地向两边裂开,一直延伸到耳根,
形成一个恐怖诡异的笑容。一个粗粝、沙哑,完全属于陌生男人的声音,
从她那秀气的喉咙里硬挤出来:“沈卫国……你,挡我道。
”沈卫国浑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,又在下一秒冻结。他几乎是凭借本能,
抓起桌上那把用来裁纸的旧剪刀,对准自己的左手掌心,狠狠划了下去!剧痛传来,
温热的鲜血立刻涌出。他毫不犹豫地将流血的手掌按向房梁上仍在嗡鸣的铜铃!
鲜血喷溅在冰冷的青铜上,顺着铃身的符文蜿蜒流淌,迅速浸透了被铁丝固定的铃舌。
那暗哑的铃舌被热血一泡,竟仿佛活了过来,
发出一种类似婴儿啼哭般的、尖锐而颤抖的共鸣音波。“啊——!
”叶知秋口中发出一声短促的、非人的厉叫,随即再次软倒下去。
而一直缠绕在她影子里的那道淡薄虚影,像是被滚烫的血液灼伤,猛地从她身上剥离,
缩进墙角阴影里,一阵扭曲变幻,最后竟化作一只指甲盖大小、通体乌黑的蜘蛛,
飞快地爬过地面,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。7 同心结,断命绳平静只维持了不到两天。
第三天清晨,峡谷如同炸开了锅——七个知青,三男四女,在一夜之间同时失踪。
没有打斗痕迹,没有告别留言,像是被浓雾无声无息地吞噬了。
公社书记老覃组织所有能动用的人力,漫山遍野地搜寻。最终,
只在落花洞入口处那片湿滑的泥地上,找到了七根头发。
每根头发都被人用鲜红的丝线精心捆扎成“同心结”的模样,但那结,却是反向系成的,
绳扣死死收紧,充满了不祥的意味,不像连结,更像是一种恶毒的诅咒,
要将两个人的命运活活勒断。搜寻无果,人心惶惶。夜里,民兵排长阿桑避开众人,
偷偷找到沈卫国。这个平日坚毅的苗族青年,此刻脸上也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。
“洞神今年……要‘娶’满九个。”阿桑的声音压得极低,像是在躲避无形的监听,
“七根头发,是七条命,已经收走了。还差两条……”他目光沉重地扫过昏睡的叶知秋,
又落在沈卫国脸上,“一条是叶知秋,另一条……是你。”沈卫国心脏狂跳,
喉咙发干:“怎么破?”“只能‘以尸赶尸’。”阿桑眼神锐利起来,
“找到最早被洞神盯上、已经遇害的人,把她挖出来。然后,由赶尸人引路,
带着这具‘尸’,走进落花洞,把洞神……‘骗’回它该待的地方。”“赶尸人?
”沈卫国愕然,“现在哪里还有赶尸人?”阿桑抬起手,指向他,语气笃定:“你就是。
”在沈卫国震惊的目光中,阿桑指向他一直简单包扎着的左手:“你的血,染了摄魂铃。
铃认主,也认血。你看你的掌心。”沈卫国下意识地解开染血的布条,掌心的伤口已经结痂,
但那深红色的血痂覆盖下的掌纹,竟隐隐构成一个清晰的、与房梁上那铜铃一般无二的图案!
像是一个刚刚烙下的、带着血腥气的烙印。8 起阴尸,画落花没有更多犹豫的时间。当夜,
月黑风高,阿桑带着沈卫国,悄悄摸到公社后山的一片乱葬岗。这里荒坟累累,野草及腰,
是历年横死、无主孤魂的埋葬之地。根据阿桑打探来的模糊信息,
他们找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包。阿桑说,下面埋的是一九五○年剿匪时,
被误作匪眷活埋的一个苗女,名叫“阿丑”。传说她生前精通蛊术,性格刚烈,
死后也不得安宁,据说有人听见坟里有异响,开棺查看时,发现她尸体不腐,
牙缝里还死死咬着半条干枯的蜈蚣。挖掘的过程沉闷而恐怖。泥土被一点点刨开,
露出底下单薄的、早已腐朽的薄皮棺材。当棺盖被撬开的那一刻,
一股阴寒的、带着土腥味的冷气扑面而出。月光惨淡,照进棺内。沈卫国倒抽一口冷气。
棺中的女尸“阿丑”,果然没有腐烂!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釉色,光滑而冰冷,
像是在窑里烧制过的瓷俑。脸庞依稀能看出生前的轮廓,五官深邃,双眼紧闭,
长长的睫毛上凝结着一层细细的白霜,宛如瓷人精美的装饰。她身上穿着破烂的苗族服饰,
颜色褪尽,双手交叠放在腹部,指甲乌黑尖长。阿桑示意沈卫国动手。
沈卫国强忍着心中的翻腾与不适,按照阿桑事先的指点,用浸过特殊药水的韧性竹篾,
将阿丑的尸体从棺中小心搬出,捆绑成一种僵硬的“站立”姿势,然后背在自己背上。
女尸冰冷坚硬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衣衫传来,让他遍体生寒。竹篾的另一端,
则缠绕在那面已经被取下、铃舌沾满沈卫国干涸血液的铜铃上。
阿桑从怀里取出一张折叠好的、颜色暗黄的符纸,递给沈卫国。符纸上用朱砂画着的,
并非传统的道家符文,而是一朵形态奇异的五瓣花朵。更诡异的是,那花朵的花心,
仔细看去,竟隐隐勾勒出人的五官轮廓,眉眼口鼻,模糊而扭曲。“这是‘落花符’。
”阿桑语气凝重,“进了洞,找到洞神的核心,你就把这张符,拍在阿丑的眉心。
她残存的怨气和蛊术,会像诱饵一样,把洞神的本体引出来。”他顿了顿,
目光如炬地盯着沈卫国,“记住,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。我已经准备了特制的土香,香点燃,